如果我們把圖像看作一個(gè)機(jī)器,那么,托馬斯·魯夫的創(chuàng)作,某種程度上就是拆卸了這些機(jī)器,以他自己的方式展示這些零件及其運(yùn)作方法。

今天,圖像就是我們的命運(yùn),圖像遍地都是,它存在于我們社交媒介的每一處,它正在改變著我們。如果我們把圖像看作一個(gè)機(jī)器,那么,托馬斯·魯夫的創(chuàng)作,某種程度上就是拆卸了這些機(jī)器,以他自己的方式展示這些零件及其運(yùn)作方法。
德國(guó)攝影藝術(shù)家托馬斯·魯夫坐在位于798創(chuàng)意廣場(chǎng)的歌德學(xué)院會(huì)客區(qū),脫下鞋子接受一家著名媒體的視頻采訪。之后不久,他和藝術(shù)評(píng)論家顧錚進(jìn)行了一次題為“缺席的相機(jī):當(dāng)代攝影藝術(shù)中的圖像認(rèn)知”的對(duì)談。對(duì)談的空間是798藝術(shù)區(qū)里典型的包豪斯建筑,這里的氣氛跟魯夫有著太多因緣:他的作品《物影照片》就是受莫霍利·納吉這位早期包豪斯的著名教師的物影照片啟發(fā)而進(jìn)行的物影照片再實(shí)驗(yàn);他也曾經(jīng)使用包豪斯第三任校長(zhǎng)路德維希·密斯·凡·德羅設(shè)計(jì)的建筑作品現(xiàn)成照片,結(jié)合數(shù)字技術(shù),加工創(chuàng)作出《L.M.V.D.R》系列作品;他于1988年創(chuàng)作的作品《房屋》系列第121號(hào),就如同798歌德學(xué)院空間的翻版。
這一天是4月14日。當(dāng)日凌晨,美國(guó)NASA宣布“土衛(wèi)二幾乎具備生命所需全部條件”。這對(duì)從小喜歡天文,且以科學(xué)攝影家自稱的魯夫來說,是個(gè)相當(dāng)不錯(cuò)的消息。比如他的《星空》和《卡西尼》系列作品就是使用從NASA購買的照片進(jìn)行再創(chuàng)作,他把這些黑白照片變成彩色,放大,制造了一個(gè)立體真實(shí)的土星現(xiàn)場(chǎng)照。而大尺寸“浸泡式的體驗(yàn)”(顧錚語),讓觀者如同身臨其境。但這恰恰觸碰了攝影真實(shí)性這個(gè)爭(zhēng)議性話題。

物影照片
科學(xué)攝影家、圖像制造者、攝影本質(zhì)的不斷質(zhì)疑者、貝歇夫婦的著名弟子及其美學(xué)主張的離經(jīng)叛道者……托馬斯·魯夫的身上帶著太多的標(biāo)簽。“這對(duì)我不公平。”魯夫在歌德學(xué)院的對(duì)話活動(dòng)上說。他已經(jīng)厭煩了別人總是問他下一個(gè)作品是什么,這下一個(gè)作品里,總是包含著由之前的作品塑造的標(biāo)簽。
1977年,托馬斯·魯夫憑借20張他拍攝的美麗風(fēng)光的幻燈片,進(jìn)入杜塞爾多夫藝術(shù)學(xué)院學(xué)習(xí),師從著名的貝歇夫婦,那一年,他19歲。在他八歲的時(shí)候,他答應(yīng)母親,信奉天主教,除非母親有一天不在了。這么多年,他信守承諾,直到前幾年母親去世,他才確認(rèn)自己不再是一個(gè)天主教徒了。更多的時(shí)間,他用來閱讀有關(guān)天文的知識(shí),直到14歲擁有人生中的第一部望遠(yuǎn)鏡,用來觀察星星,“本可以成為一個(gè)天文學(xué)家,只可惜自己太懶。”
在杜塞爾多夫藝術(shù)學(xué)院的第一個(gè)作品,是拍攝中產(chǎn)家庭的《室內(nèi)》,走的還是貝歇夫婦堅(jiān)持拍工業(yè)建筑遺跡的類型學(xué)路子。只是不久,由于很多家庭要裝修,他不得不中斷這個(gè)主題的拍攝,開始拍攝周圍朋友的肖像。魯夫也試圖開辟另一條路子,這條路不同于德國(guó)傳統(tǒng)肖像里的路數(shù),比如奧古斯特·桑德的肖像那樣攜帶著人類學(xué)的信息,在魯夫這些名為《肖像》的作品中,從人物表情上看不到更多的內(nèi)容。“他可以是皮特,也可以是任何一個(gè)人。”魯夫說。這組被稱為“無表情”的作品后來成了魯夫最著名的作品。盡管有批評(píng)家評(píng)價(jià)該作品為“深刻的平庸”,但在評(píng)論家顧錚看來,這組作品試圖重新定義人。如果說,貝歇夫婦的美學(xué)主張是確定一個(gè)主題一直拍下去,那么魯夫后來的創(chuàng)作,正好與這個(gè)主張分離。他甚至撇開相機(jī),以圖像現(xiàn)成品來進(jìn)行各種探索和實(shí)驗(yàn)。

星空
托馬斯·魯夫是個(gè)有歷史感的藝術(shù)家。這一點(diǎn),國(guó)內(nèi)的相關(guān)解讀很少涉及,大部分介紹都立足于他對(duì)攝影語言的實(shí)驗(yàn)與自治,從而將他“打扮”為一個(gè)歷史虛無主義者。比如他的《物影成像》以莫霍利·納吉的作品圖為物品,制造了一個(gè)虛擬的物影成像的現(xiàn)場(chǎng)。這種創(chuàng)作顯示出魯夫?qū)τ趥鹘y(tǒng)的有效激活。他的新作《媒體++》,是從日本和美國(guó)等通訊社上世紀(jì)60年代的圖片里找到一些資料,這些圖片資料的正面或背面都有編輯寫下的評(píng)論文字。這些文字簡(jiǎn)單而粗暴,在魯夫看來,是圖片遭遇了一種極其惡劣的命運(yùn)。所以他將這些圖片、評(píng)論文字,甚至印戳,進(jìn)行蒙太奇的拼接。他要展示的正是這種媒體內(nèi)容生產(chǎn)者施加于圖片的暴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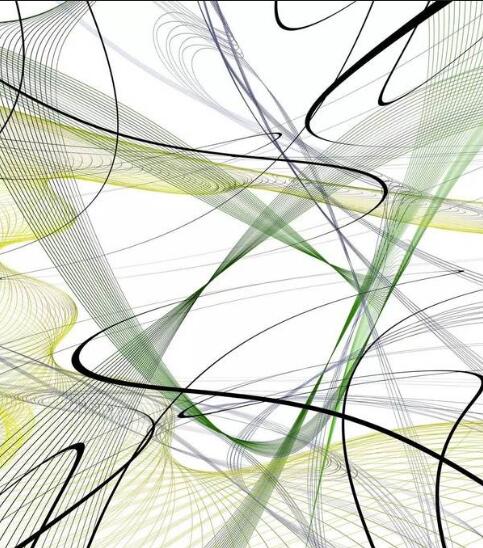
Zycles
托馬斯·魯夫,幾乎成了攝影語言實(shí)驗(yàn)的代名詞。當(dāng)然,這些實(shí)驗(yàn)都是基于已有圖像或圖像樣式。比如他的《裸體》,是將網(wǎng)絡(luò)上下載的色情照片進(jìn)行模糊化處理,探討看不見和“想看見”的欲望體驗(yàn);他在《報(bào)紙照片》里,將作為新聞插圖的圖片從新聞中抽取出來,放大展出,剝離新聞賦予的意義,恢復(fù)圖片作為圖片本身的尊嚴(yán);《Zycles》系列的3D數(shù)字曲線圖,靈感來自19世紀(jì)電磁學(xué)書籍上的銅版畫,魯夫用電腦數(shù)字建模后再用2D的方式呈現(xiàn),將彩色線條和漩渦噴墨打印在帆布上;《卡西尼》系列,是他將從NASA買來的黑白火星照片轉(zhuǎn)為彩色,并進(jìn)一步轉(zhuǎn)變?yōu)?D照片。他改造和實(shí)驗(yàn)的基底,甚至包括日本動(dòng)漫和各種檔案照片。
他創(chuàng)作立足的不僅僅是攝影,更在于寬泛的圖像以及其中的各種問題。他將圖像作為工具來探討其中的哲學(xué)問題,或者圖像背后人的操縱意志和人對(duì)圖像意義的額外賦予,他激活傳統(tǒng)的具有歷史感的東西去進(jìn)行新的創(chuàng)作。
他甚至試圖為攝影在藝術(shù)史上爭(zhēng)取一種地位。比如,托馬斯·魯夫、古斯基、托馬斯·斯特魯斯、坎迪達(dá)·霍夫等杜塞爾多夫?qū)W派的藝術(shù)家,開辟了攝影大尺寸展示的先河。在魯夫看來,大尺寸使攝影從二級(jí)藝術(shù)變成一級(jí)藝術(shù),具有了和繪畫同等的地位。
而在中國(guó),也有一些藝術(shù)家在作品實(shí)踐上與魯夫的思路對(duì)話。如張大力的《第二歷史》,探討的是圖像里政治權(quán)力的運(yùn)作機(jī)制;而武漢的藝術(shù)家組合李郁和劉波,以現(xiàn)實(shí)新聞為基礎(chǔ),以劇場(chǎng)排演的方式創(chuàng)作,亦在追問攝影這一媒介或攝影的語言到底是什么。
今天,圖像就是我們的命運(yùn),圖像遍地都是,它存在于我們社交媒介的每一處,它正在改變著我們。如果我們把圖像看作一個(gè)機(jī)器,那么,托馬斯·魯夫的創(chuàng)作,某種程度上就是拆卸了這些機(jī)器,以他自己的方式展示這些零件及其運(yùn)作方法。
托馬斯·魯夫的中國(guó)之行,對(duì)于中國(guó)觀眾來說,似乎是一次驗(yàn)證行為,驗(yàn)證對(duì)他的各種想象。有趣的是,他對(duì)任何一個(gè)問題的回答都是樸素的,甚至可以說是具體的形而下的。這就給評(píng)論家們出了道難題,那些被闡釋得高高在上的作品,如何才能回到藝術(shù)家創(chuàng)作的初衷?
我不想突出誰更重要,我希望給所有人使用一樣的燈光
人物周刊:你是貝歇夫婦的學(xué)生,這一點(diǎn)我們都知道。但后來,你是貝歇夫婦的所有學(xué)生里,美學(xué)主張和觀點(diǎn)跟你的老師離得最遠(yuǎn)的一個(gè)。你進(jìn)入杜塞爾多夫?qū)W院后,最初是因?yàn)槭裁磸年P(guān)心現(xiàn)實(shí)問題轉(zhuǎn)向?qū)iT關(guān)心攝影語言本身?
托馬斯·魯夫:實(shí)際上我也不知道為什么,可能有一個(gè)原因,我那時(shí)候19歲,并不認(rèn)識(shí)很多人,我并不認(rèn)識(shí)所有的學(xué)生,我不知道要去拍攝什么。我想我就是拍一拍我的朋友們,所以我的攝像機(jī)就拍我的同學(xué)和朋友。

夜
人物周刊:比如說,你很快就從中產(chǎn)階級(jí)家庭轉(zhuǎn)到肖像的拍攝上。
托馬斯·魯夫:我必須承認(rèn)在那個(gè)時(shí)候拍過中產(chǎn)階級(jí)家庭的主題,我終結(jié)了這個(gè)主題,因?yàn)橐婚_始室內(nèi)的拍攝就遇到了許多問題。比如,很多室內(nèi)要進(jìn)行裝修,我們沒有辦法拍攝室內(nèi)主題了。當(dāng)時(shí),我還認(rèn)識(shí)一些朋友,他們成立一個(gè)朋克樂隊(duì),我有照相機(jī),可以去拍一些照片。他們說托馬斯·魯夫你要給我當(dāng)導(dǎo)演,我就說好吧,謝謝你們,我很愿意給你們拍一拍照片,而且我也能夠給他們拍一些肖像照。
當(dāng)時(shí),在杜塞爾多夫?qū)W院有一個(gè)研討會(huì),是由本雅明·布赫洛主持的,他曾經(jīng)探討過關(guān)于柏拉圖 “洞穴”理論的概念,以及一些極簡(jiǎn)主義的藝術(shù)概念。所以當(dāng)我能夠去拍一些肖像照的時(shí)候,我希望盡量進(jìn)行一種極簡(jiǎn)主義甚至觀念主義的處理。我希望避免所有傳統(tǒng)的對(duì)待肖像的態(tài)度和行為,我希望能夠重返這種極簡(jiǎn)的肖像,我也希望剪除所有那些讓我們分散注意力的東西。
傳統(tǒng)的肖像,意味著過去的很多攝影師,他們希望能通過光和影去解讀一個(gè)人物的性格,我并不想這么做。我認(rèn)為那個(gè)時(shí)候我們生活在一個(gè)西方工業(yè)化的時(shí)代,比如說我們都采用工業(yè)燈光照明的停車場(chǎng),停車場(chǎng)的燈光是很均勻的。所以,我想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我的模特,我希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拍攝人,我不想突出誰更重要,我希望給所有人使用一樣的燈光。因?yàn)樗麄兌际俏业呐笥眩瑳]有誰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。
人物周刊:沒有一個(gè)作品不帶有操縱行為或者痕跡。其實(shí)在你的作品中,你竭力剔除一些闡釋中所引申的意義,力爭(zhēng)回到作品本身來思考。但問題是,你現(xiàn)在的作品恰恰需要大量的描述和闡釋,我們才能走得更近,你本人怎么看待這種悖論?
托馬斯·魯夫:我覺得這個(gè)很有意思,你剛才說得很對(duì)。當(dāng)我做肖像的時(shí)候,有很多人很不高興,說只能看到肖像的臉。同時(shí)我在作品的說明上,只寫了“肖像,1986”,沒有任何附加的標(biāo)題,觀眾不知道這個(gè)肖像里的人是誰,年齡是多少,不知道是干什么的,職業(yè)是什么。
通常情況下,很多攝影師是需要提供這些背景信息給觀眾的,因?yàn)檫@不是一幅肖像,是三到四幅肖像,它是匿名的,每一個(gè)人的臉和其他人都不一樣,而且觀眾能感覺到。比如從肖像里面看到的人是你,但是對(duì)于我來說,他是皮特,或者是任何一個(gè)人都可以。
我1981年開始做這些肖像的時(shí)候,我那一代的很多人在讀奧威爾的小說《1984》,當(dāng)時(shí)我們都很好奇,有些人把這個(gè)小說當(dāng)科幻小說看,說1984年是什么樣的,會(huì)不會(huì)城市里面到處都有攝像師,會(huì)不會(huì)有人監(jiān)視我們等等。
當(dāng)時(shí)我22歲,我們也聽朋克,大家都希望自己看起來很帥很酷的樣子,所以我的肖像當(dāng)時(shí)是很酷的感覺。同時(shí)我想創(chuàng)作我們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形象,他在看到攝像機(jī)的時(shí)候是沒有表情的,是冷漠的,你不知道肖像里面的人想什么,我沒法捕捉。
人物周刊:這里面有一個(gè)關(guān)鍵詞——冷酷。我很好奇,這些表情看上去冷酷,或者說這些作品似乎顯得理性、冰冷,那么,情感對(duì)你來說意味著什么?
托馬斯·魯夫:我覺得相機(jī)只能夠反映它面前的東西,相機(jī)本身就是一個(gè)無感情的東西,所以你怎么用相機(jī)記錄感情呢?怎么得到這種感情呢?

人物周刊:但所有拍攝的指令都不是由相機(jī)發(fā)出的,是由人發(fā)出的。
托馬斯·魯夫:對(duì),攝影師站在這個(gè)肖像后面,你看這個(gè)肖像的時(shí)候,你會(huì)覺得這個(gè)肖像也看著你,但實(shí)際上他沒有看著你,在那一刻,他們是看著相機(jī)的。
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悖論,可能沒有辦法來解決這種悖論。
所有人都希望汽車能夠開得更快,更快,更快
人物周刊:你后來的創(chuàng)作中,使用了數(shù)字計(jì)算、3D建模、截屏等一系列手段,這些都是數(shù)字時(shí)代的典型特征,數(shù)字化是你深入討論攝影的一個(gè)出發(fā)點(diǎn)嗎?
托馬斯·魯夫:實(shí)際上數(shù)字化攝影到來的時(shí)候——我覺得可能在中期——我并不關(guān)心我們用膠片技術(shù)還是數(shù)字化的技術(shù)拍照片,我覺得差不多嘛。用數(shù)碼技術(shù)拍照片,只是一種新的濾鏡,使用新的設(shè)備拍照,我覺得沒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但是我認(rèn)真地思考數(shù)字化攝影,是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時(shí)代到來的時(shí)候,所有圖片都可以在因特網(wǎng)上找到,所以不是數(shù)字化改變了攝影,而是數(shù)字化圖片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的分發(fā)和傳播改變了攝影。
我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技術(shù)拍照片,這只是當(dāng)代的實(shí)踐。我也是當(dāng)代的藝術(shù)家,我當(dāng)然會(huì)使用當(dāng)代的一些技術(shù),為什么不使用呢,為什么一直使用老派的技術(shù)呢,像過去的暗房技術(shù)洗膠片。我覺得可以用任何方式,可以是膠片攝影,也可以是數(shù)字化攝影,我認(rèn)為我感興趣的是圖像,我感興趣的是真實(shí)。
人物周刊:對(duì)你作品的闡釋,大量的評(píng)論還是把你作為一個(gè)媒介的探索者。在我看來你的作品可能含有社會(huì)批判的成分,比如我們?cè)诳础堵泱w》的時(shí)候,里面有關(guān)于欲望的探討;看《另一種肖像》的時(shí)候,有對(duì)圖像與權(quán)力的討論。
托馬斯·魯夫:也許在一開始的時(shí)候,我并沒有這么去思考這些作品。實(shí)際上我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,就是來自我的日常生活,吃早飯,上班,看電視,讀雜志,讀報(bào)紙。有時(shí)候我看到一些東西,很感興趣,或者讓我很焦慮,讓我不安,我不能把這些東西排除出去,我不得不連續(xù)地思考,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?jiǎng)?chuàng)作。
這種事情經(jīng)常會(huì)發(fā)生,最初的想法來自我看到的東西。舉一個(gè)例子,比如說《物影成像》系列,我曾經(jīng)從美國(guó)的一個(gè)畫廊買了兩幅照片,掛了幾年,我每天都看他們,然后在某一個(gè)時(shí)間點(diǎn)上,我突然覺得可以做一個(gè)自己的物影成像作品,這是我的工作方式。有時(shí)候我想找到一個(gè)攝影作品的歷史,關(guān)于物影成像,關(guān)于其他藝術(shù)家的來源。
物影成像是這樣的,你去暗房里拿到一個(gè)感光紙,拿一個(gè)物品放到感光紙上,打開燈光,看到物體的影子留在感光紙上面,你把相紙拿開之后,你確定尺寸是不變的。我不喜歡把東西放到相紙上面,你打開燈,比如我希望這個(gè)剪子的角度往左邊再挪兩公分,那怎么辦,必須得重新再來一遍,這是很復(fù)雜的事情。
物影成像的作品全都是黑白的,但實(shí)際上我有25年都是拍彩色的照片,我希望有顏色,我希望能夠產(chǎn)生這么一種虛擬的暗室,有這種虛擬的相紙,虛擬的物體,無論是紙還是金屬、或者虛擬的燈光。我一直在使用3D渲染軟件來使用這種暗房,我覺得這種不夠先進(jìn)。我有一個(gè)朋友是技術(shù)人員,幫我做了一個(gè)更先進(jìn)的暗房,你可以事后去編輯這個(gè)相紙的大小。把燈光打開的時(shí)候,可以使用有顏色的燈光,我們最后使用彩色的物影成像作品,這就是我的創(chuàng)作過程。我看到很吸引我的東西,我就去創(chuàng)作或者再創(chuàng)作,我希望找到這么一種當(dāng)代化攝影的方式,有時(shí)候會(huì)成功,有時(shí)候會(huì)失敗。
人物周刊:你的當(dāng)代化是體現(xiàn)在媒介的當(dāng)代化特征,或者說是大家都在使用的媒介上面嗎?
托馬斯·魯夫:實(shí)際上我希望能夠創(chuàng)造一個(gè)物影成像作品。在2012年的時(shí)候,我希望模仿1920年代物影成像的照片,事實(shí)上,有些圖像是沒有被人見到過的,所以我想創(chuàng)作出一些前所未見的作品,超出1920年的局限。

肖像
人物周刊:那超出這種局限的意義在哪里?
托馬斯·魯夫:這就好像是汽車公司一樣,所有人都希望汽車能夠開得更快,更快,更快。
在大的尺寸出來之前,攝影被認(rèn)為是二級(jí)藝術(shù)
人物周刊:我們聊聊關(guān)于尺寸的問題。你的《肖像》系列在早期是很小的尺寸,后來做了兩米多的尺寸去展出。在德國(guó),我們可以看到古斯基和沃爾夫?qū)ぬ釥柭挂彩褂么蟪叽纭T谥袊?guó),有王慶松、封巖、楊泳梁,甚至一貫以小尺寸展出的鳥頭小組也開始制作大尺寸作品。那么,除了市場(chǎng)神話之外,大尺寸在當(dāng)代攝影的表達(dá)上到底存在哪些必要性?
托馬斯·魯夫:我覺得很簡(jiǎn)單,大的尺寸實(shí)際上是把攝影藝術(shù)解放出來,真正讓攝影藝術(shù)成為了一級(jí)藝術(shù)。在大的尺寸出來之前,攝影被認(rèn)為是二級(jí)藝術(shù)。第一個(gè)原因是,一個(gè)藝術(shù)家使用一個(gè)機(jī)器去創(chuàng)作作品,很多人認(rèn)為他不是藝術(shù)家。如果他創(chuàng)作的作品只有這么小,很不錯(cuò),但還不是真正的藝術(shù)。
當(dāng)我開始把我的一些肖像放在藝術(shù)畫廊展出的時(shí)候,我看到人們站在這些作品前面,是很不可思議的。人們沒有辦法忽略這些作品,比如像現(xiàn)在的這些收藏者,原來可能沒有注意過這些,一旦站在面前,看到的肖像的表情和準(zhǔn)確度確實(shí)發(fā)生了變化。這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攝影原來的概念,而且使攝影進(jìn)入到現(xiàn)代藝術(shù)當(dāng)中。
人物周刊:我很好奇那些你沒有實(shí)驗(yàn)成功的作品。
托馬斯·魯夫:我二十多年前一直想拍好一些關(guān)于花的照片,但始終沒有滿意的結(jié)果。我動(dòng)用了各種手段,最后還是暫停了,但這個(gè)愿望還在。
人物周刊:你的作品也一直在試圖回到觀看本身,也就是說在觀看之外沒有意義。那么我想問一下,你怎么看那張土耳其海灘上趴著的敘利亞男孩的照片?
托馬斯·魯夫:那是張偉大的新聞?wù)掌?/span>
0
喜歡他,就推薦他上首頁吧^_^

CND設(shè)計(jì)網(wǎng)(CNDESIGN)會(huì)員所發(fā)布展示的 “原創(chuàng)作品/文章” 版權(quán)歸原作者所有,任何商業(yè)用途均需聯(lián)系作者。如未經(jīng)授權(quán)用作他處,作者將保留追究侵權(quán)者法律責(zé)任的權(quán)利。
Copyright ©2006-2019 CND設(shè)計(jì)網(wǎng)
移動(dòng) Android 版
豫 ICP 備16038122號(hào)-2
 豫公網(wǎng)安備 41019702002261號(hào)
豫公網(wǎng)安備 41019702002261號(hà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