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永和,1956年生于北京,父親是著名建筑師張開(kāi)濟(jì)。他在八十年代自費(fèi)赴美留學(xué),先后在美國(guó)波爾州立大學(xué)和加利福尼亞大學(xué)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分別獲得環(huán)境設(shè)計(jì)理學(xué)士和建筑碩士學(xué)位。自1993年起,張永和成立了“非常建筑工作室”并開(kāi)始在國(guó)內(nèi)從事建筑設(shè)計(jì)、實(shí)踐。經(jīng)過(guò)三十多年在建筑領(lǐng)域的摸索,張永和設(shè)計(jì)出了二分宅、席殊書(shū)屋等等作品,并成為了普利茲克獎(jiǎng)評(píng)委團(tuán)里的首位中國(guó)面孔,被稱(chēng)為“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主義建筑之父”。16日下午,霧霾籠罩著北京城。我們從出租車(chē)上下來(lái),在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尋找著張先生的工作室所在地,期間差點(diǎn)走錯(cuò)路。還好,我們找到
張永和,1956年生于北京,父親是著名建筑師張開(kāi)濟(jì)。他在八十年代自費(fèi)赴美留學(xué),先后在美國(guó)波爾州立大學(xué)和加利福尼亞大學(xué)伯克利分校建筑系分別獲得環(huán)境設(shè)計(jì)理學(xué)士和建筑碩士學(xué)位。自1993年起,張永和成立了“非常建筑工作室”并開(kāi)始在國(guó)內(nèi)從事建筑設(shè)計(jì)、實(shí)踐。經(jīng)過(guò)三十多年在建筑領(lǐng)域的摸索,張永和設(shè)計(jì)出了二分宅、席殊書(shū)屋等等作品,并成為了普利茲克獎(jiǎng)評(píng)委團(tuán)里的首位中國(guó)面孔,被稱(chēng)為“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主義建筑之父”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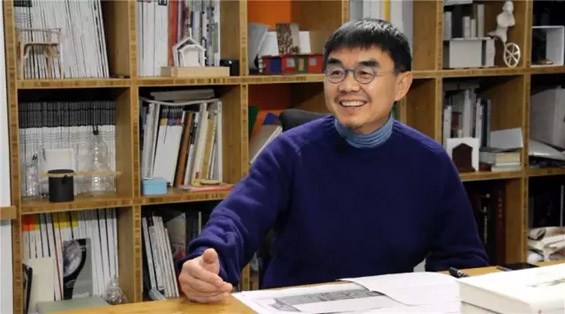
16日下午,霧霾籠罩著北京城。我們從出租車(chē)上下來(lái),在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尋找著張先生的工作室所在地,期間差點(diǎn)走錯(cuò)路。還好,我們找到了那棟四層小樓,而張先生的工作室“非常建筑”就在這棟樓的頂層。
我們走進(jìn)去時(shí),整棟樓似乎都在裝修。木板、水泥一類(lèi)的工地用料堆放在一樓的大堂里,仿佛是北京的一個(gè)縮影——日新月異的今天,即使你曾經(jīng)來(lái)過(guò)這里,也可能會(huì)迷失在完全不一樣的景觀中。
與外面的裝修形成反差,張先生的工作室很安靜,井井有條。哪怕是很小的細(xì)節(jié),也充滿(mǎn)了十足的設(shè)計(jì)感。我們走進(jìn)張先生的辦公室。空氣里彌漫著好聞的木質(zhì)家具的味道。這是一間并不算寬敞的屋子,最引人注目的,是墻上掛著的一張莫蘭迪的油畫(huà)——幾只簡(jiǎn)單到極致的瓶子,那是莫蘭迪的經(jīng)典題材。除此以外,屋子里就只有辦公桌和簡(jiǎn)單的書(shū)柜、書(shū)架以及幾把椅子。桌子上擺放著各種圖紙、書(shū)本和辦公器材,凌亂中隱隱透露著秩序。
我們調(diào)試好器材,等待著張先生。不一會(huì)兒,張先生走了進(jìn)來(lái)。他開(kāi)了整整一天的會(huì),但看起來(lái)沒(méi)有絲毫疲憊,溫和地配合著我們的種種要求。這次,他要在鏡頭前讀一首詩(shī),是美國(guó)詩(shī)人弗羅斯特的代表作《雪夜在林邊停留》,他說(shuō),這首詩(shī)能夠給他帶來(lái)一種“寧?kù)o的感覺(jué)”——這與他對(duì)于古典建筑理念的推崇有著某種契合之處。
于是,我們從詩(shī)歌談到了建筑,之后又聊了聊繪畫(huà)和攝影,以及其他一些我們感興趣的話(huà)題。
楚塵文化:之前了解到您曾提出過(guò)一個(gè)概念,古典與“理想城”。古典建筑的理念在哪些方面最吸引您?
張永和:在中世紀(jì)的歐洲城市,其實(shí)是沒(méi)有建立起“透視”概念的。所以當(dāng)時(shí)的人們對(duì)縱深感、空間感并沒(méi)有形成為一種審美。到了后來(lái),人們有了這種審美的意識(shí),就發(fā)現(xiàn)以前城市的組織方式是不夠的。
中世紀(jì)的街道都是在城堡里,有防御性的需求,都是彎曲的。后來(lái)人們意識(shí)到城市也可以有筆直的、縱深感非常強(qiáng)的街道時(shí),已經(jīng)是文藝復(fù)興早期了。第一個(gè)畫(huà)這個(gè)的畫(huà)家,他把自己畫(huà)筆下的城市空間命名為“理想城”。因此“理想城”是純建筑的,與烏托邦的理念一點(diǎn)關(guān)系也沒(méi)有。
古典建筑最吸引我的地方,在古典音樂(lè)里也有。當(dāng)然不是說(shuō)全部,我主要指的是巴洛克時(shí)期的古典音樂(lè),比如巴赫就是特別好的例子。古典的音樂(lè)與建筑的美學(xué)都是一致的,都建立在一種非常安靜的氛圍里。那種寧?kù)o,其實(shí)是跟人的心理需要是一致的。也許對(duì)我來(lái)說(shuō),我非常需要這份寧?kù)o,我在音樂(lè)里也好,建筑中也好,獲得的是一樣的東西。簡(jiǎn)單地說(shuō),就是這種安寧感特別能打動(dòng)我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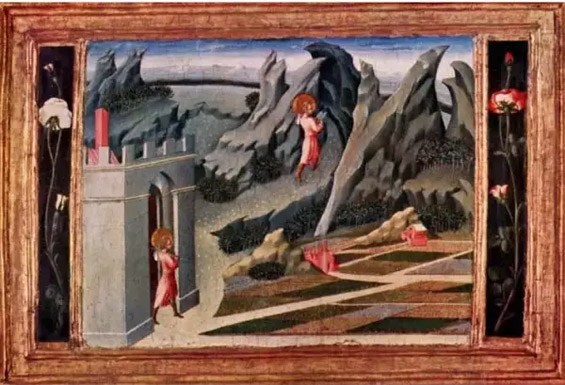
圣約翰走向荒野
楚塵文化:您好像很喜歡莫蘭迪的畫(huà)?
張永和:莫蘭迪是其中之一。西方繪畫(huà)從文藝復(fù)興早期,一直到1960年代,我都很熟悉。其中有很多我都非常喜歡。當(dāng)然,每個(gè)畫(huà)家對(duì)我的影響是不一樣的。莫蘭迪也是有一種安靜,同時(shí)也有一種質(zhì)樸。
除此以外,從技術(shù)上講,莫蘭迪把畫(huà)處理得很“平”,等于是幾乎沒(méi)有空間。這個(gè)我感覺(jué)特別有意思。比如說(shuō),我喜歡用手機(jī)照相,手機(jī)拍出來(lái)的照片就做不到這一點(diǎn)。所有的空間都擠在一起,這樣的效果很奇特。我自己也喜歡畫(huà)畫(huà),但我的技巧特別差,凡是不強(qiáng)調(diào)技巧的畫(huà)家的作品我一概都喜歡,德·基里科、西羅尼等等,缺少技巧的畫(huà)家常常會(huì)創(chuàng)造出一些奇妙的空間。
楚塵文化:為什么會(huì)喜歡用手機(jī)拍照?
張永和:照相我一直都喜歡。但手機(jī)與相機(jī)不同的是,相機(jī)面對(duì)的是實(shí)際的世界,而手機(jī)鏡頭里其實(shí)是已經(jīng)成型的效果。我可以把它在拍照之前就轉(zhuǎn)成黑白效果,那么我可以看到光的質(zhì)感。
楚塵文化:您喜歡森山大道嗎?
張永和:如果說(shuō)日本攝影師,我最喜歡植田正治,尤其喜歡他拍的時(shí)尚照片,還有村子里的一些照片。他這個(gè)人跟我的興趣很像,都喜歡杜尚。
楚塵文化:我身邊的一些朋友有時(shí)會(huì)抱怨,中國(guó)的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,沒(méi)有特色。您認(rèn)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么?
張永和:這其實(shí)是一個(gè)誤會(huì)。誤會(huì)是源自?xún)煞矫娴模环矫媸谴蠹也⒉涣私狻俺鞘惺窃趺葱纬傻摹保?dāng)然也就無(wú)法想象。實(shí)際上,城市的形象是整個(gè)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(huì)操作的產(chǎn)物。一個(gè)城市的面貌一樣還是不一樣,不是愣造出來(lái)的。在過(guò)去,南方的城市,比如說(shuō)泉州,它有一些磚的砌法,磚頭的顏色等等等等,跟一個(gè)北方的城市,比如說(shuō)山西的城市,肯定是不一樣的。而現(xiàn)在是工業(yè)制造,大家都是一樣的工序,當(dāng)然的面貌也就變得一樣了。其實(shí)單純地想要城市不一樣是很容易的。你比方說(shuō),把天津的房子全都刷成綠色,那天津自然就有特色了,但這是一種裝飾性的特色,不是本質(zhì),也沒(méi)有多大意義。
另一方面,這其實(shí)反映了現(xiàn)代人的某種“旅游心態(tài)”。現(xiàn)在新型城市的問(wèn)題不是千篇一律,而是都不宜居。過(guò)寬的馬路,過(guò)大的街區(qū),很不完善的商業(yè)、文化、服務(wù)的設(shè)施網(wǎng)絡(luò)等等。現(xiàn)在很多人出去旅游,覺(jué)得怎么到處都一樣啊,但反過(guò)來(lái),如果把自己居住的房子改造得不一樣,我們未必會(huì)接受,反而會(huì)說(shuō),怎么我的跟別的地方設(shè)計(jì)的不一樣啊。這就是游客心理。
其實(shí)你去歐洲,城市也都差不多。他們的城市情況比較好,很宜居,但看上去也都差不多。你從俄羅斯到挪威,肯定會(huì)有差異,但微觀地看,一個(gè)法國(guó)的城市,和一個(gè)德國(guó)的城市,其實(shí)也差不多少。
二分宅(或稱(chēng)山水間、土宅)
楚塵文化:“二分宅”您是根據(jù)北京的四合院作為雛形的,突出了建筑與環(huán)境的關(guān)系。西方的人與環(huán)境的觀念,與中國(guó)的自然觀念,有何異同?
張永和:西方的整個(gè)空間思維,是從物體開(kāi)始的。對(duì)于西方人來(lái)說(shuō),首先要有一個(gè)東西,這個(gè)東西放在這里了,占了這個(gè)空間了,這里的空間就存在了,反之沒(méi)放東西這空間就不存在。中國(guó)則完全不一樣,最容易舉的例子就是圍棋,先預(yù)設(shè)一個(gè)空間,所以中國(guó)的空間是最直接的,西方就多了一個(gè)步驟。這就導(dǎo)致西方的建筑是占領(lǐng)式的,征服自然,這在以前的中國(guó)是沒(méi)有的,中國(guó)不講究征服自然。西方到了現(xiàn)在,一定程度上也受了東方理念的影響,也開(kāi)始想要融入自然。這個(gè)理念對(duì)西方是新的,對(duì)中國(guó)來(lái)說(shuō)是舊的。
所以中國(guó)建筑不應(yīng)該只學(xué)習(xí)西方,應(yīng)該多看看咱們的鄰居,比如斯里蘭卡。
0
喜歡他,就推薦他上首頁(yè)吧^_^

CND設(shè)計(jì)網(wǎng)(CNDESIGN)會(huì)員所發(fā)布展示的 “原創(chuàng)作品/文章” 版權(quán)歸原作者所有,任何商業(yè)用途均需聯(lián)系作者。如未經(jīng)授權(quán)用作他處,作者將保留追究侵權(quán)者法律責(zé)任的權(quán)利。
Copyright ©2006-2019 CND設(shè)計(jì)網(wǎng)
移動(dòng) Android 版
豫 ICP 備16038122號(hào)-2
 豫公網(wǎng)安備 41019702002261號(hào)
豫公網(wǎng)安備 41019702002261號(hào)